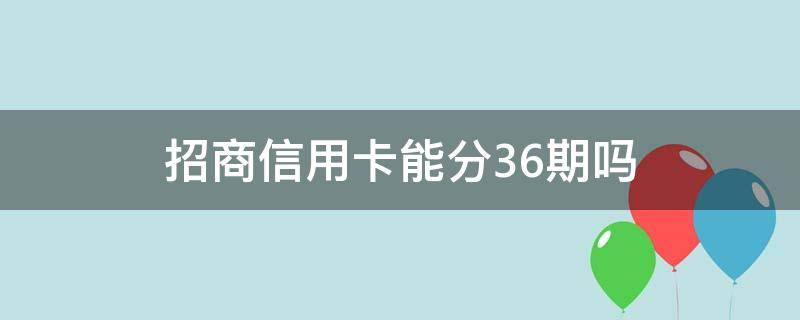摘要:房星感觉心里也经历了一场汹涌的洪水——对父母存积了10多年的抚养照料问题,在极端时刻集体迸发了。
“我们这儿的水都没过车轱辘了,你要把车停到高的位置!”
7月31日上午,房星微信里收到一条父亲扯着嗓子喊的语音。76岁的父亲因为11年前一次脑卒中,双耳几乎失聪,一直和老伴住在房山区养老。语音背景里传来噼里啪啦的雨声,房星知道,那是雨点砸在自家小院顶棚的声响。
在这位老人的世界里,这场雨并无大碍。他反倒更惦记女儿的车。
但他不知道,自己所处的房山区,已成为北京强降雨的核心重灾区——根据北京市气象台消息,7月29日以来,全市遭遇140年以来降水量第一的持续性大暴雨。7月31日全天,北京房山区平均降雨量和门头沟区平均降雨量皆超过400毫米,远高于2012年北京“7·21”暴雨量级。房山区等7个乡镇62个村通信信号中断,同时,房山区主供水管道冲毁,区内大面积停水。暴雨不仅冲击了道路和信号塔,更冲垮了许多山区和城市郊区地带空巢老人和城里子女脆弱的连接。
7月31日下午,民间救援力量在网络上自发建立了“北京暴雨求助信息统计汇总”腾讯共享文档。8月1日下午2点左右,房星无助之际也登记了父母信息:“两名行动困难的76岁老人和一名57岁的保姆被困在家,停水停电停煤气,手机马上断电即将失联……”
截至8月2日下午6时30分,这份表格已经将求助范围扩大到京津冀多个城市,信息总数达1028条。在这些求助信息中,有400多条提到“老人受困”,备注中常有“独居”“基础病”等说明。
等待的时间里,房星感觉心里也经历了一场汹涌的洪水——对父母存积了10多年的抚养照料问题,在没水没电没网的极端时刻集体迸发了。

7月31日,洪水涌入小区。受访者供图
无声的“求助信号”
收到父亲微信语音的当天,45岁的房星有了立刻回父母家的冲动。父亲半身瘫痪,母亲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伴有糖尿病尿酮症,平时只能委托住家保姆照顾。她上次回家还是2个月前。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?你回来替我了,我也好回自己涿州家里看看。”保姆顾阿姨在电话像往常一样发问,但这次语气添了些无助。此时房山的暴雨已持续两天。
房星回父母家的路不算远,从朝阳东五环到房山琉璃河,70多公里,1个多小时的车程。但现在她被这场磅礴的暴雨困住了。
下暴雨的第二天,她开车出发,刚上京港澳高速公路就遇到了路障。一路上她不断看到折返的人。近处的积水里,可以看到零星被泡的小轿车,她只能返回。
房星开始感到恐惧。她叮嘱父母关手机,减少耗电,防止失联。住家保姆成了两个老人的“紧急联系人”。
房星父母住在滨水雅园小区西门附近的33号楼1楼。西门相比东门,地势更低。大水从西门漫进来后,水位逐渐上升到人的大腿根。

积水最深时,房星父母院子里的家具都漂浮起来了。受访者供图
7月31日,房星开始不断拨打父母居住小区的物业、所属村委会、镇政府以及应急抢险部门电话。她收到回复:救援队已全部派出,正在一线抢险,已到达琉璃河镇上。
但小区内,不见救援队的身影。房星猜测,可能父母那边“救援优先级不高”,毕竟小区附近还有整个村都被淹了的情况。
8月1日下午,顾阿姨的手机电量快耗尽。棘手的是,因为通信基站在大雨中损毁,家中几乎没有手机信号。当天下午,顾阿姨冲到隔壁楼信号好一些的邻居家中,请邻居转告房星:“还差一个台阶水就要漫进家里了。”这是小区断电断水的2天半里,顾阿姨唯一一次联系上房星。
后来,房星再也打不通顾阿姨电话了。情急之时,她脑海里闪现的是父亲床头那盏忽明忽暗的应急灯。“自从我爸爸脑血栓以后,他就没法儿待在全黑环境里,我不知道停电以后这盏灯还能亮多久……”
付蕾与住在门头沟的父母失联前,最后一次通话停留在7月31日早上10点30分。
电话里,父母告诉她,村里水势很大,出村路被淹。有村民想往山上高处撤离,但“山上在不停地往下冲水,走不好就面临被冲的风险”,村里不允许村民私自撤离。
“后悔死这个决定了。”事后回想,付蕾说父母本可避免这次险情。
虽然付蕾父母也是空巢老人,但和大多数家庭情况相反,他们平时在北京城里住,而付蕾是自由职业者,不坐班,住在门头沟区的浅山区。
7月底,付蕾出京了一趟,但她不放心家里宠物,就让父母帮忙去山里看家。没想到遭遇暴雨。
和父母失联后,付蕾给村里邻居挨个发消息,都没有答复。
她打电话给门头沟区应急办,获知各镇已向区里打卫星电话,报人员平安,但未透露救援进展。付蕾很忐忑,门头沟山里面的村子里,居民住得分散,很可能只能自救……
她一刻没有停止在网上搜罗讯息,小红书、微信、微博……但没有人知道王平镇和东马各庄村的确切消息。
而在房星家里,涨水的小院里,户外的茶几、沙发都漂浮在水上,篱笆里母亲在生病前精心种植的玫瑰花只露出了花苞,成了水生植物。
小区里60岁以上老人约占居民数三分之二以上。保姆顾阿姨能探听到的消息有限。
8月1日下午晚些时候,她看到窗外有零星的人在洪水里,拿着水桶跋涉,立即询问,才知道小区东门口来了水车,能免费打水了。
家里两个老人好几天没擦身子了。“房星妈妈吃的控制血糖的草药也快没水煮了。”她决定蹚水出门打水,朝头上套了一个黑色大垃圾袋防雨,手里拄着一根家中院子里找来的长木棍。
“我只有1米5多点的个头,路上水已经齐我腰了。”水桶装上水后,顾阿姨发现水桶可以在洪水里漂浮起来了,她只要推着桶走就行了。这是她说起这场洪水时,唯一脸上带笑的故事。
这天,到小区门口四五百米的路,顾阿姨来回摸索了近2个小时。但打到水后,厨房里堆积如山的脏碗她依旧没敢洗。

房星父母家厨房,积攒了多日的碗筷因为缺少生活用水都没有洗。 杨书源 摄
吃什么在那几天也成了问题,没有电和燃气,热菜热饭成了奢望。做房星妈妈这位糖尿病患者的餐食更是为难:家里主食就剩下3个馒头,但不适合糖尿病病人。每顿饭顾阿姨就掰下小半个馒头,再拿出几根生芹菜,一碟酱油,让房星妈妈蘸着吃,“芹菜能让她血糖升慢点”。
顾阿姨自己不敢吃太多,每天就吃点零食充饥。“神经高度紧张,也不觉得饿。”和外界失联的那几天,她似乎失去了时间概念,每天都很恍惚。

一位老年人在小区里涉水。受访者供图
暴雨中的小院
8月1日中午,房星意外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,电话里母亲的声音有些困倦。
“妈,您怎么拿顾阿姨的电话在打,您都好吗?”房星有些意外。因为这一整天通讯网络太差,顾阿姨都很难拨通房星的电话。
“这是我的手机,我都挺好的……”母亲慢条斯理地说。
对于母亲的这通电话,房星有些意外。母亲确诊了初期老年痴呆后,整个人时而糊涂时而清楚,手机也不记得充电,基本上平常就是关机状态。“可能她内心深处始终有这么一两个惦记的人。”房星感慨道。
这个电话,成了洪水时期母女俩的秘密。甚至是顾阿姨,也不知道房星母亲是在何时脱离了她的视线、又如何拨通了这个电话。

房星的父亲和母亲在堆着不少杂物和快递的家中。杨书源 摄
“我非常后悔! ”说起十多年前安置父母的决定,房星的声音突然提高了,“我当时就应该强制让他们搬过来一起住。”
她曾多次提议父母搬到城里的电梯房,和自己住一段时间,但都被父母拒绝了。理由是:父亲现在必须推着支撑架行走,平衡感差,在人多的地方被轻轻一碰可能都会倒地,所以他排斥在高层公寓楼里坐拥挤的电梯。此外,父亲是个注意细节的人,他担心“和闺女住,夏天太热时,想在家光膀子也不好意思”。
房星没有再强求,“有时想想,如果同住,我妈会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,我父亲因为耳朵不好,每天都要把电视调到很大声,似乎觉得分开住也是最相安无事的安排。”
房山这套三室两卫带小院的一楼房子,是十多年前父亲在脑卒中发作前瞒着家里买的。此前老两口住在天通苑某小区6楼,退休后上楼日渐费力。父亲发病后,母亲在帮父亲收拾东西时才发现了这套房子的购买凭证。当时父亲已经行动不便,一家人决定临时装修。之后父母两人住了进去。
当时一切还算令人满意。客厅墙壁被生性浪漫的父亲刷成了淡粉色。家里被母亲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她刚退休,特别爱往外跑。即使父亲生病,她也常带着他去海南、北戴河度假。
但浪漫理想的晚年图景,被老人独居生活的琐碎、艰难一点点侵蚀。父母生活急转直下是从今年年初开始,当时母亲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。
其实母亲得病,早已有迹可循——最近一两年回家,房星忽然发现,家里各个角落被垒成小山状的快递盒子占满。不少盒子里都放着过期保健品,都是母亲电视购物买回来的。
顶峰时期,家里天天都有快递上门,连快递员都打电话给房星:“你快拦着你妈吧,哪儿有这样天天给人保健品公司送钱的!”
还有一回,天气阴冷,母亲忽然跑出家门,躺在小区角落里一个被遗弃的脏沙发上睡觉。被家里人唤醒时,她还笑眯眯地说:“我觉得这儿能晒太阳挺好的。”
现在回想起来,房星才意识到,这都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前期症状,但她一直理解为母亲性格中的执拗、一意孤行。
去年冬天疫情高峰时期,房星叮嘱父母不能出门,母亲变得十分嗜睡疲软,无人照管后她变得嗜吃零食,血糖控制得很差。最严重时,从房间走到客厅都要歇上好几次。房星意识到了情况不妙,带母亲线上问诊了专家,确诊了是阿尔兹海默症……
暴雨过后的一天,记者在房星的委托下,入户探访两位老人,却被房星爸爸当成了推销员。他努力扶着支撑架走到老伴儿跟前,不断打断使眼色,害怕老伴儿又上了“保健品骗子”的当。
雨后的家中,有种憋闷潮湿的气味。房星母亲因为停电停水多日没能洗澡,一头短发被汗水浸透后又出油,自动拢成了一缕缕小发束;父亲因常年不出门活动,身体笨重硕大,挪步艰难。
现在房星父母都患上了脑神经系统的疾病,母亲表现得淡漠迟钝,父亲则烦躁警惕,夫妻俩交流越来越少,常常一人坐沙发、一人坐餐椅,沉浸在各自的世界。
偶尔,父亲会硬把躺在沙发上的母亲拽起来,认为“这么躺着对身体不好”。交流又演变为激烈的争吵。
顾阿姨文化程度不高,但从老两口的对话中,知道这对老夫妻是大学同学,“年轻时都是很厉害的大设计师,在北京城里盖了不少有名的建筑。”
现在顾阿姨每天的职责之一,就是提醒房星母亲不要睡着,“她每天必须出去走五六百米,也不能午睡太久,这样可以延缓小脑萎缩。”她对家政公司的培训内容信手拈来。
只是暴雨这几天,老人一直困在家里,“越呆越疲软、人发蔫儿”。但这些事儿,顾阿姨都没和房星说。“她隔得那么远又过不来,说了也没用。”
“其实我也挺想回家看看的。我家是涿州的,也遭了水。”在这个家里,她总是会忘记,自己也已是一个57岁、偶尔需要人照料生活的“准老年人”。
“银发”抗洪自救团
几天的困境,将赡养父母的问题重新推到房星面前。
“你才发现,无论是父母还是我自己,都困守在城市孤岛上了。”房星形容。上一次经历这种绝望,是在去年冬天新冠疫情高发时期。但无论如何,上次他们还能远程沟通,而现在,她能做的只有无尽的等待。
小区被淹、父母失联的两个晚上,房星都是抱着手机睡觉。她不时惊醒,又忙着刷新业主群消息。
顾阿姨识字不多,房星担心她漏掉重要的信息。

小区退水后,随处可见曾经防汛用的沙袋。 杨书源 摄
在小区里,她能托付的人也不多,大多数熟人都是身体不好的空巢老人。好在同一栋楼3楼有一对60多岁的热心夫妻,也是从城里搬来养老。以前母亲身体好时还常给他们送菜、约着一起去汗蒸。听顾阿姨说楼道开始进水时,房星联系了这对夫妻,作为父母的保底选择:一旦水淹到了家里,就让父母上3楼避险。
父母家斜对角1楼也住着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,男主人退休前是律师。房星拜托他,万一家里有什么突发情况,请他过去。老人承诺,“如果有什么事,就算是蹚水也要过去帮你看看。”
身边贴身照顾的是老人、能求助到的也是老人,弱者帮助更弱者,成了洪水孤岛里,脆弱而可靠的求生链。
很快,居民们都陆续收到了琉璃河漫堤的消息,水向地势较低的北面倒灌。滨水雅园小区就是受灾的小区之一。7月31日下午,楼里的积水落下去了,但晚上又涨起来。
8月1日早上,小区里为数不多的青壮年自发去西门外拉政府提供的防洪沙袋。业主群里,有人提议,低层住户每户出一位劳动力去小区外指定地点搬沙袋。

8月1日,居民在搬运抗洪物资。受访者供图
第一轮动员,群里报名的只有8人。组织者只得再度动员。
许久,有人回应:“家里都是行动不便的老人,怎么出人?”有许多人开始附和发声。微信群随后陷入了沉默。
“那就年轻点的老年人出来自救。”小区里69岁的住户孙锐就是站出来的人之一。
水不断从西门往小区里灌时,大家连夜在西门垒起了四五米高的沙包墙,还找来渣土车运了一车碎渣乱石才勉强堵住了洪水。洪水堵住后,大家又商量着如何排水。
“参与抢险的基本都是五六十岁的男士,在这个小区,这都算上好的壮劳力了。组织者倒是一个大妈。”讲起当天“抗洪抢险”的经历,孙锐觉得无奈又好笑。他的右侧小腿在这场自救中受了伤,创口贴不能完全覆盖的伤口隐约可见。“不少人的脚都被水里卷着的碎石玻璃划了很深的口子。”孙锐说。到了第二天清晨,小区内的积水基本都被排尽了,只留下深深浅浅的淤泥。

8月2日,小区积水都已经排出,围堵西门的泥沙袋还未撤走。 杨书源 摄
相比而言,在山村,空巢老人自救的空间更局促有限。
8月1日下午,付蕾发现网上开始流出附近村庄失联人员信息,“有些相对年轻体能好的,自己徒步翻山走出去了,把我们相邻7个村的大致信息带出去,又把救援人员领进去。”
从8月1日下午到夜里的几个小时,付蕾收到大量从山里传出的报平安信息。不少是村里的空巢老人主动跑到手机信号强些的邻居家,给子女报平安的。他们说,村里来了救援队。下午6点左右,付蕾终于收到了一条邻居的回复——她家里人都平安。
8月2日早晨9点左右,与家人失联将近48小时的付蕾也终于收到了母亲借别人手机发来的短信,简短的一句竟然是:“我们都安全,路都断了,千万不要回去!”
当时门头沟深山区的一些镇子依旧没有失联人员消息。“门头沟的山太深了,整个门头沟区可能90%以上全是山,我们在浅山区还好,官兵靠走还能进去,但是深山区根本不可能走进去。越是深山,住得越多的就是没有自救能力的留守老人……”付蕾说。
房星记得,父母搬到这里时,是在2012年的夏天,也赶上了那年北京“7·21”特大暴雨期间,“小区没有被淹得这么严重,周边还布置了防洪沙袋。后来北京确实没下过什么暴雨,即使下雨的时候偶尔停电也都习惯了。”
房星的父母入住后才发现;小区里前后左右的邻居不少是来自北京城区的退休夫妻。当时老人们常会讨论和子女同住的话题,大部分人觉得“不到万不得已别住在一起。”他们退休前大多经济状况不错,精神和物质上都不想依赖子女,看重这里“房价只有三四千元、可以住一楼带独院的房子、附近有大超市、湿地公园”。
历经十多年以后,入住时还矍铄、精干的老人们衰老了。而与之相对的是,小区环境越来越差。“头几年还行,后来越来越不济。莫说环境和物业服务了,这小区平时根本就没人管。”孙锐回忆。
老人和小区一起老去了。洪水退去之后,整个滨水雅园愈发萧条,小区内道路全都被淤泥覆盖,潮湿泥泞,黑色的泥浆和散落的生活垃圾混在一起。白天气温升高,路面上的污泥、脏水散发出阵阵腐烂的臭味……

洪水退去后,小区里满是泥泞。 雷册渊 摄
洪水退去后,离开还是继续独居?
“外面的泥浆水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清理干净。”房星的母亲在暴雨退却后动过暂时离开小区的念头。她在窗边喃喃自语:“这儿环境太差了,早就想走了。”那一刻,她似乎恢复了早年间精明能干的模样。
这时已是8月2日下午2点多,小区周边的道路都已恢复通行。小区里也已经通电,自来水还没有来,手机信号时断时续。
小区快递驿站的老板也回店里打扫。暴雨后的第一批快递到了。最多的货物是子女在网上远程给老人送来的成箱饮用水。

恢复物流后,快递驿站收到的第一批物资是子女给家里老人网购的成箱饮用水。杨书源 摄
房星找外卖员送来了两大袋外卖。平时母亲一看到外卖就会兴奋。但那天,不知怎么,母亲看着这些饭菜,兴趣索然。
这天小区里的老人越来越少。“谁家老人被子女接走了”之类的消息,在老人间流传。此时33号楼里只剩下房星父母家一家住户了。
其实8月2日清晨,这栋楼里还有两家住户。顾阿姨早上开门时,发现自家楼道不像别的楼道一样泥浆水泛滥,显得异常干净。后来她才知道,是3楼那对老夫妻清晨6点起来,去小区东门水车那儿一趟趟打水,再浇水、清洗,干到了午饭时间,才把楼下这块地冲洗干净。
但很快,打扫成果遭到破坏:顾阿姨没看住家里的狗。狗独自出了楼道,去泥浆水里跑了一圈回来,楼道又沾上了泥。平时温和谦逊的老夫妻,严肃地下楼敲门告诫顾阿姨看好狗。“或许经历了这一遭,老人们都在承受难以言说的压力。”房星说。
下午,不断有老人在周边采买物资时滑倒的消息传来。住在房星父母家楼上的老夫妻踌躇再三后,决定回市区暂避。

8月2日,小区地面上还是一片泥泞。一对老年夫妻打水归来。雷册渊 摄
房星原本也计划把父母接到家附近住。“起码让父母在我身边,先把这个夏天过去吧……”她发动同事帮忙,在家附近租一个可以容纳父母和保姆的两居室。房子基本谈妥了,她打电话告诉父母和顾阿姨时,却遭到了反对。
母亲不知为何改变了想法。她说:“我们不去,这儿都没事了……”顾阿姨也不愿意离家几十公里做住家保姆,在电话里停顿了好久憋出一句:“那你们试着找找别的阿姨吧,我去不了……”听到异口同声的回绝,房星一时也没了方向。

8月2日,房星家退水后的院子一片狼籍。 杨书源 摄
小区里没走的老人也不在少数。
不少心急的老人开始自己摸索着出门,到自家仓库抢修被水泡过的电器、电动车。“都是我儿子从城里搬来的,也不知道他还用不用,先检查了再说。”一位大妈在自家车库里收拾得焦头烂额,拖鞋上都是泥泞。
刚参加完一夜“抗洪”的孙锐也闲不住。他披散着头发、打着赤膊出来了,拿着一把铁钩清理自家楼栋门前的淤泥和垃圾。

暴雨后,房星父母家楼上的邻居一早起来把楼道冲刷干净了。杨书源 摄
孙锐看起来乐观豁达,拒绝把自己塑造成“孤岛老人”的角色。他说,淹水那天不仅是孩子一家,还有很多远在外地的亲戚朋友发来问候。
当被问道现在水退了,孩子有没有来看望时,他连连摆手说自己并不需要。“路还没通呢,不麻烦他们,不麻烦……”
孙锐打趣说:“暴雨那天,我们这儿上了新闻,孙子打来视频说,爷爷你们小区可以游泳了。你瞧瞧,他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,多好玩儿……”
房星经历了半天的内心挣扎后,也放弃了让父母搬到城里的执念。她不断拨打市政、物业电话,恳请工作人员为小区做洪水后的消杀,但一直未果。她下定决心,周末前赶完手边这几天耽误的工作,就回房山接替顾阿姨。“到时,我替爸妈收拾小院,做一次里外彻底的消杀。”
不过,“如果再有任何变数,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把他们接走。对于他们的生活的艰难,我已经错过太多了!”
房星没有把握,经过这场暴雨涤荡之后,她和父母内心的距离,将会变得更远还是更近……

退水后,小区内一对老夫妻在抢修儿子的打印机。杨书源 摄
(文中房星、付蕾、孙锐为化名)